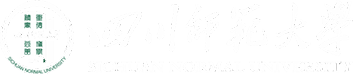近日,我校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吴超明、刘文强先后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从三星堆文化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历程》和《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堵”与“疏”》。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从三星堆文化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历程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出土了造型奇异的青铜器、风格独特的金器、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十分珍稀的象牙等文物,展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独特审美、高超技术与神秘仪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三星堆与蜀文化的研究热潮。三星堆文化从夏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区,地处中原与西南夷地区之间,还是中原青铜文明向西南传播的前沿阵地和关键纽带,体现出夏商文化、蜀文化和西南夷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历程提供了重要视角。
因夏而生
进入青铜时代以前,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着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了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为三星堆文化的诞生提供了优渥土壤。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是东亚的中心文化,也是中国早期国家初步发展阶段的重要代表。夏代晚期,夏文化进入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进而沿长江上游水道西进至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封口盉、敞口觚、高柄豆等日用陶器在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夏文化的玉璋、玉戈、绿松石铜牌、单翼铜铃等也被三星堆文化吸收,成为重要的祭祀用品。总之,夏文化的传入打破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格局,三星堆文化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中形成,夏文化因子也成为三星堆文化中长期留传、不断发展的新要素。据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可能与夏代移民的南迁有关。
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关系集中反映在铜器上。从形态上看,三星堆圆尊的造型与中原二里岗、殷墟的圆尊接近。兽面纹尊的造型与殷墟二期的大口尊接近,而兽面纹的一些细部特征与湖南出土的同类器相似。龙虎尊与安徽阜南出土的同类器几乎一致。罍的造型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接近,但有些罍体形高大、高足直立的形态特征和兽面纹、凤鸟纹的纹饰特征又与湖南岳阳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可见,这些铜器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淮河中上游等地的商文化关系密切。从技术上看,无论是尊、罍等来自商文化的铜器,还是立人、面具、头像、神树等极具古蜀特色的铜器,它们的合金配比都以锡青铜、锡铅青铜为主,铅青铜为辅,属于中原商文化的合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铜器的范铸成型技术与中原一致,铸造使用的泥范又与长江中游接近,这说明三星堆文化铜器制造业的兴起应该是中原商文化青铜铸造技术进入长江中游后向长江上游传播的结果。总之,在商文化的影响下,三星堆文化的生产力迅速提升,制造了大量造型独特的铜器、玉器、金器等古蜀重器,修建了面积约3.6平方千米的巍峨古城。此时的蜀文化已经是十分成熟的青铜文明,具备了将原始信仰作为精神纽带来行使统治权力的古国形态。
向夷而兴
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长期的发展和巴人的涌入导致成都平原的人口数量大幅增长,三星堆文化的都邑也由三星堆古城迁移至金沙遗址。金沙遗址面积约5平方千米,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相似的金器、玉器、象牙等祭祀用品。成都平原以金沙遗址这一新都邑作为中心聚落,形成了众星拱月的聚落布局。在金沙遗址西北面约20千米的郫都区有一处波罗村遗址,这个遗址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拱卫金沙遗址、管理一般聚落的次级中心聚落。在中心和次级中心聚落的周围,涌现出大量面积小于10万平方米的一般聚落,形成了多层级的金字塔式聚落结构。同时,陶器制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金沙遗址修建了160余座陶窑,是四川盆地最大的陶器制造中心,次级中心聚落与部分一般聚落也修建了小型陶器作坊,完全能够满足成都平原日用陶器的供应。可见,三星堆文化迁徙都邑后,并没有继续在营建城墙、制造大型青铜器等显示贵族身份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投入大量资源,而是快速推进中小型聚落营建、陶器制造等与普通居民生计关系密切的生产活动。这是三星堆文化合理调配资源、稳定社会局面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古蜀国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成都平原内部日益繁荣,三星堆文化迅速对西南夷地区产生较深的文化影响。
三星堆文化向西南进入青衣江中上游(今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雨城区、眉山市洪雅县一带),翻越大相岭后进入大渡河中游(今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汉源县一带),向南沿青衣江、岷江进入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的交界区域(今四川省南部宜宾市屏山县一带),向东南沿长江上游东进,再南下进入乌江下游(今重庆市东南部酉阳县一带)。三星堆文化扩散覆盖至这些地区,涌现出一批扼守古蜀南界的聚落。这使得西南夷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前述西南夷地区进入了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将这些新兴聚落作为战略据点,继续向西南传播至安宁河谷(今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州一带)、滇东黔西地区(今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巧家县、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威宁县一带),向南传播至赤水沟通黔北(今贵州省北部遵义市习水县一带),向东南传播至黔东(今贵州省东部铜仁市碧江区一带)、湘西地区(今湖南省西部怀化市芷江县一带)。这些地区保留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但与古蜀国保持着通畅的文化商贸往来。此外,三星堆文化中极具夏文化特色的玉璋还辐射到遥远的岭南及越南等地。
总之,通过内外策略的调整,三星堆文化不仅解决了成都平原内部人口骤增的问题,还将其转化为解放生产的有利条件,并主动向南进行文化传播。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明进入全盛阶段,通过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水系将其影响覆盖至四川盆地南部边缘地带,催生了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明,并继续向长江上游以南的广阔天地传播,将华夏文明因子辐射到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
多元一体
中原夏商文化是东方文化圈的中心,蜀文化是东方文化圈的西南边缘,西南夷文化又是蜀文化的南部边缘。它们区域不同,特色明显,反映出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特征。但是,蜀文化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进入青铜文明,西南夷文化在蜀文化的影响下进入青铜文明,并将文明因子继续南传。从黄河到长江,从中原到西南,这实际上就是中国青铜文明由中心向边缘逐渐扩散的一体化进程。蜀在夏夷之间,既是指在东方文化圈内区位的衔接,又是指进入青铜文明的年代早晚衔接,更重要的还是指文化功能上的衔接。在夏商文化南传的广阔图景中,蜀文化不但是发展最迅猛、特色最鲜明的区域文明之一,而且发挥了关键的桥梁纽带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青铜文明的扩散。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之一,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历程无疑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进程提供了关键证据和重要视角。
原文发表于2025年02月07日《学习时报》。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堵”与“疏”
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较多,如芍陂、郑国渠、漳河渠、灵渠等。其中,较为完美诠释“堵”与“疏”的两种治水理念的则是两个水利工程:一个是近些年考古发现的建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公元前256年修建而成的都江堰。
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良渚水利工程其实是一个高、中、低三级水坝系统,通过人工垒筑的高低错落的土坝群,阻水于山间及平原的地势低矮处,起到阻挡洪峰等作用。其中,岗公岭等山谷谷口水坝群组成高坝系统,现坝顶海拔25—35米,坝体宽60—80米。大遮山脉和塘山间新发现的多条长垄为中坝系统。鲤鱼山水坝群等组成低坝系统,现坝顶海拔9—10米,坝体宽50—100米。当山洪和暴雨来临时,高坝系统可首先阻水于山谷中,中坝系统可应对洪峰外溢的二次冲击,低坝系统最终阻拦漫溢洪水于低地,并将多余水量定向排出。这种高、中、低三级坝体的配合,不仅可以有效地应对暴雨和山洪,三级坝体形成的水面也能起到很好的水上运输等作用。
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秦国郡守李冰率众修建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以无坝引水闻名世界。其工程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疏导和分流系统,主要是通过打通玉垒山宝瓶口以及筑造分水堤起到分流和引水的作用,实现了江水流向以及流量上的控制,进而起到集分洪、引水灌溉和航运等于一身的作用。现工程主体为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典籍中记载的“壅江作堋”即是在江中筑分水堤,主要起到将岷江水流分向内外二江的作用。宝瓶口位于玉垒山脚,由开凿玉垒山而形成,是内江进水的咽喉。飞沙堰是位于分水堤下段和宝瓶口之间的一段低堰,主要起到泄洪和排沙的作用。
这两个水利工程突出体现了一“堵”一“疏”的建造理念。良渚水利工程的多处堤坝体现了先民对“堵”的执着,都江堰的分水引水很好地诠释了“疏”的偏好。客观而言,这两个水利工程的理念侧重不同,更多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状况对于该地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两个水利工程修建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便是因地制宜改善原区域不适宜文明发展的原有自然及水文地理环境。
良渚水利工程所在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山洪的肆虐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先民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对农作物等也有着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对当地这一极易引发山洪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便显得尤为重要。成都平原在都江堰修建之前有着水患与干旱两方面的自然环境问题。以岷江河道为界,以西外江区域在多雨季节经常受到洪涝灾害等水患威胁,时常冲毁农田及民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岷江以东区域又经常连年干旱,农作物灌溉用水及民众生活用水均较为缺乏,对农业发展及人民生活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岷江河道进行引水分流也便极为迫切。
良渚水利工程利用天目山系南麓的天然谷地,在谷口狭窄位置筑以堤坝,巧妙地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容水库区,直接便可以拦截多雨季节的暴雨,避免了夏季暴雨对于下游古城区域的直接冲击。都江堰则是在岷江流出山地进入平原的出山口,用火烧冷水浇的自然方法开凿了异常坚固的玉垒山山体,形成了可供分流引水的宝瓶口,而后又在宝瓶口上游的岷江河道内,用与修筑良渚水坝相通的方式构筑金刚堤以改变水的流向,使更多的合适的水量进入宝瓶口。都江堰的修建重新分配了原岷江河道东西两侧的水量,使得原来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西岸不再易涝,亦使得原来较为干旱的东岸得到了有效灌溉。
从表面来看,良渚水利工程和都江堰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设计和建造理念。良渚水利工程相较而言更类似于文献记载中鲧惯用的“堵”的做法,都江堰则和鲧之子大禹常用的“疏”的治水方法颇为相合。然而换个角度进行考量,这两个水利工程的建造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通的。
良渚水利工程利用多个坝体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容水库区,可以阻挡洪涝于其库区之中,以达到防洪和航运等目的。其做法初看是堵,然则两个库区的容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永远只进水而不出水,因此,低坝库区必然会有专门的泄洪口或泄洪槽。因而,良渚水利工程系统不可能仅仅是“堵”,它的堵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有目的有方向的“疏”。
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而闻名。如今二王庙的墙壁之上还有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法水则,将治水方法中的一个“疏”字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其竹笼中装石砌筑而成的位于岷江中心的分水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堵”——堵水之外江去路以引之内江,当然这种“堵”也是为了更好的、有目的性的“疏”。
从良渚水利工程三个坝区的蓄水库容来看,其若是发生溃坝事件,那对于良渚古国的人群来说将是致命的,而良渚人群在太湖流域能一直持续到距今4300年左右,至少说明在这约700年的时间内,良渚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稳定的,也说明其约700年间一直在发挥功用。都江堰则是通过历代不断地修缮与维护,持续两千余年不停地造福着四川盆地的人民。
良渚水利工程系统和都江堰因为自然环境及治水目的的差异,从而在建造理念侧重方面有着不同的体现。然而从深层次考虑,良渚水利工程的“以堵控疏”及都江堰的“为疏而堵”在实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根据因地制宜而践行的治水理念。而通过中国早期这两个水利工程所体现的“堵”与“疏”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鲧的“堵”还是大禹的“疏”,从治水方法上来说其实也并无孰优孰劣。无论是侧重于“堵”还是侧重于“疏”,只要前期妥善建造,后期合理维护,均能持续数百年而不溃。
原文发表于2025年02月21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