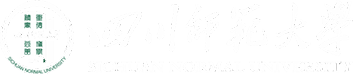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网成都讯(记者 陆航)5月11日,“历代三苏图绘研究学术沙龙”在成都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召开。会议由三苏研究院主办,三苏祠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聚焦历代三苏图绘形象展开多学科研究交流与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文涛、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分别致辞。三苏研究院副院长刘开军主持开幕式。

学术交流现场 陆航/摄
图绘形象体现文化品味
相比较历代文人,苏轼也许是传世画像最多者。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朱万章在发言中从国家博物馆藏品的角度展示了大量的苏轼的图像绘画。苏轼画像分两类,一为独立半身像,一为整身像。此外,在文集或一些版画、碑刻中,也不乏苏轼画像,但多为线描画。这些画像都是在宋元画迹基础上的传移模写,保持了苏轼头戴东坡巾(东坡帽)、右颊有黑痣、有稀疏的胡须、相貌儒雅、身材中等特征。朱万章表示,苏轼传世独立肖像画之外,在《西园雅集图》、《东坡笠屐图》、《东坡退朝图》、《赤壁图》和《眉山翰墨图》等故实画中亦可见苏轼小像。其独立的画像大多有据可依,可追根溯源。而故实画中的苏轼画像,有的来自于传移模写,有的来自于想象图之。由这些画像的生成与传播可以看出,苏轼在文学、书画等方面的杰出造诣,影响后世深远,成为千余年来后世文人崇拜的对象。正因如此,其画像在元明清以来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以降,每个文人心中都驻着一个不一样的苏轼。基于对苏轼及其文学、艺术的推崇,每年固定的寿苏会(拜苏会)成为苏轼画像生成的重要途径之一。除临摹之作外,画家们大多从自身的角度为我们诠释了不一样的苏轼。朱万章认为,不同时期、不同画家绘制的不同形象的苏轼,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苏轼的接受史及其艺术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
如何理解历代图绘中的苏轼形象?在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潘殊闲看来,人们对苏轼的形象一直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苏轼的形象,与真实的苏轼、也就是肉身的苏轼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一文化现象说明,文学经典与艺术经典、文化名人与名人文化的互通、互摄、互促与互进。由苏轼丰富有趣的形象演变史,可以折射出苏轼永恒的人生魅力与艺术魅力。《西园雅集图》之所以在历史上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不断加以摹写,并以绘画、诗词、雕刻等艺术形式不断重现,就在于这种“雅集”,是集文学、书法、绘画、抚琴、谈禅、论道、弈棋、品茗等为一体的艺术沙龙,最典型地体现了北宋文人那种诗意的栖居。
西园雅集发生于北宋元祐时期。王诜邀请苏轼、蔡肇、李之仪、苏辙、黄庭坚、李公麟、晁无咎、张耒、郑嘉会、秦观、陈景元、米芾、王钦臣、圆通大师、刘泾。共16人集于府邸西园,或观书,或题石,或挥毫,或抚琴,或论道,成为西园雅集的历史事件。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杉从视觉研究角度聚焦西园雅集图。陈杉提出,宋以后的园林雅集类活动组织和图像绘制,客观上受到了西园雅集活动范式的影响。在雅集参与人群上,文人与僧侣共游园林论道已成为普遍现象,“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大夫结纳”。在雅集活动上,以琴棋书画为媒介的活动形式最为常见,鉴赏古玩、观演话剧、清谈说经等多元活动成为园林雅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个体情感表达和诗意化生活的方向得到持续发展。

学术交流现场 陆航/摄
据苏轼本人的撰述,秀才何充、僧人妙善、程怀立、道士李得柔以及李公麟等,都曾经为他绘制过画像,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无一留存于世。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韩旭辉以《三苏图绘中的服饰研究———以苏轼为例》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苏图像绘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以《却对金莲烛:“烛送词臣”绘画主题与苏轼典故的图像化传播》为题,以苏轼图像研究出发,分析图绘形象体现着文人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和文人雅士恬淡的文化品味。

学术交流现场 陆航/摄
借鉴图像思考诗和画的关系
绘画可以视觉形式呈现诗的审美效果,展示诗的历史深度,追求诗的精神境界,获得与诗歌媲美的艺术品格。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陈琳琳通过题为《图像视域下的苏轼诗歌阐释与传播研究》的发言,展示了石涛以其所擅之画,与苏轼所长之诗竞赛,企图为绘画争取与诗歌平等的地位。藉由对东坡诗意的援用与创造性阐发,石涛使其绘画蕴含了诗的情致与意趣,具备了诗的格调与品位。陈琳琳提出我们可以借鉴图像研究方式研究苏轼的诗歌,进而思考诗和画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城市纪念空间,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中具有纪念功能或纪念行为的建筑或场所。所谓“苏轼图绘”,即与苏轼有关的图像和绘画。清代道光年间,苏州城定慧寺旁新建苏公祠,其中出现了专门以苏轼图绘为核心要素的纪念空间。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研究员成荫以《寺院、士人与艺文:清代苏州城的苏轼图绘纪念空间》为题,从社会文化空间介绍清代苏轼图绘。成荫认为,苏公祠这一纪念空间以苏轼图绘为载体,与三个因素相关。一是寺院,二是士人,三是艺文活动。成荫围绕苏轼图绘、寺院、士人、艺文活动四个要素,简要梳理清代苏州城苏轼图绘纪念空间的演变和基本特征,通过这一个案观察苏轼图绘纪念空间在苏轼纪念空间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寺院、士人与苏轼图绘纪念空间的紧密关联。
山川诱发怀古的迷思,怀古离不开自然的存在。山川登临为现实与历史的交融提供了场域,也为有限与无限的接续提供了入口,它叠印着历史的痕迹,触发着登山者形而上的生命感受。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一楠以《“我辈复登临”:〈后赤壁赋〉与赤壁登临图的意涵空间》为题分析了环形空间叙事。王一楠表示,“环形空间叙事”图像模式将承载较多叙事信息的陆地场景,环绕画面中央承载较少叙事信息的水域展开;在此结构中,山与水的相对位置重建了原文本的空间逻辑,唯有依赖观看者的想象力,具有时间逻辑的情节进展才得以复原;时空关系的视觉变革,进而使多处场景被展示为无人之境,大片的画面空间留给了不具有叙事性的荒山与野水,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空幻虚静的氛围。王一楠认为,赤壁登临图与同时代绘画对文人之游的表现方式密切相关。对赤壁的登临与游观,以一种当下直击的方式,确认了画中人苏轼的历史性存在。

学术交流现场 陆航/摄
创新三苏文化传播路径
纵观苏轼的一生,虽然在仕途上遇到过王珪这样的庸相及其亲信李定、何正臣、舒亶,还有章惇等阴险“小人”,但更多的是欣赏和敬仰其才华的命中贵人,如宋神宗、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欧阳修、张方平、王安石、王巩,以及各地的地方官。在个人生活上,少年时有父母的言传身教,得志时有王弗的红袖添香,深陷漩涡时有弟弟的庇护、王润之的柔肠和儿孙等家人的陪伴,风烛残年时还有朝云的白首不渝,儿子的全身心照顾。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最幸运的文人!四川师范大学三苏研究院教授魏华仙以《苏轼的幸运》介绍了苏轼的人生遭遇。魏华仙认为,正是苏轼的幸运,他才能在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受到当时人的爱戴与崇敬并将这种爱戴与崇敬延及当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君以《苏轼的对夏立场与文学》从文学角度对苏轼的宋夏立场进行了探讨;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邓永江以《三苏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译介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为题,论述苏轼是中华多民族的苏轼。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馆员陶晓姗以《胤禛弘历父子的东坡情缘》为题,通过梳理馆藏宫廷书法、宫廷教育文物,展示胤禛弘历父子对苏轼的书法字体的喜爱、学习。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郑轶以《三苏图像数字化再现与新媒介技术传播》为题目,提出运用数字化、新媒介技术适应当下艺术表现形式,由原先的被动接收转化为具有趣味性地主动接受来传播三苏文化。

学术交流现场 陆航/摄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燕以《自喜渐不为人识——东坡笠屐图砚赏析》分析了其豁达乐观的处世态度。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曾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传承与创新———从苏轼的“活法”说起》为题,通过回顾苏轼独特的处世态度,拓展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曾明认为,当我们穿越岁月的厚重幕幔,不难发现,苏轼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宝,特别是他重“活法”有温度的诗文,细读检讨,常思常新。这些并不是字的排列组合,而是流淌的岁月生命,生命是会延续的。正如眉州之山,钟灵毓秀;岷江之水,清澈灵动。这或许是苏轼从宋朝走到今天,成为中华文化底色的原因。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曾明提出要发挥文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巨大作用。一是相关研究结果不应该仅停留在狭小学界和有限书斋,要从专业的学术层面走向广阔的现实应用,应该流布在社会和广大老百姓心中;二是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有拿得出手的优秀文艺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力争实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三是注重形式方面的突破创新,把中国的经典和音体美、衣住行结合起来,以开放的思维,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原文网址: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5/t20240512_5750692.shtml